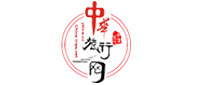汤小铭,1939年生于广西桂林。著名油画家,国家一级美术师。1959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附中,1964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,进入广东画院任专业画家。历任广东省文联委员、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常务副主席、主席等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,省美协名誉主席,广州美术学院院外教授、暨南大学兼职教授,广东画院艺术顾问、广州美协艺术顾问,“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艺术委员会”委员。 油画、连环画、国画、书法俱佳,尤擅油画肖像。主要作品有《永不休战》《女委员》《虎门民兵》等,多次获国家级奖项,并被多家机构收藏。



汤小铭:我的油画之旅
2022年12月24日,第三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、著名艺术家汤小铭因病去世,享年83岁。本版刊发其生前文章,以表缅怀。
初中毕业,家境欠佳,我面临几个考虑,一是继续考高中,一是出来工作,但也想报考中等专业学校,如艺术师范或美术中专之类学校。因为既符合自己的爱好,又不需缴学费,还管伙食。那时正好在报上见到中南美专附中在中南五省招生的告示,太好了,于是欣欣然写信去武汉报名。对于我的这个决定,家里人并不赞成,认为是一种没多大出息的志向。曾看过一部电影,里面就有个靠吃南瓜当饭过日子的画家。那时我不明白,他们总认定当画家就得受穷。穷就穷吧,是自己情愿的,年少气盛的我,还不知道过穷日子的难受。
才不过十五六岁,我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,决意要走自己选定的路。假如考不上怎么办?心里也做好了打算,我会一面留在武汉找活干,一面准备再考,直至考上为止。考完试就在一个初中同学的家里耐心地等待学校放榜。有了打算,心情倒也轻松,和同学去东湖里游泳,到珞珈山的绿荫中闲逛。苍天不负有心人,终于在《长江日报》登出了美专附中的录取名单,我惊喜异常地在报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,高兴极了,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,即刻我就搬到学校去住。我的艺术生涯即由此开始。
好几次与同学一道,揣上馒头渡江到汉口的展览馆去参观苏联油画。太激动了,在这之前,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外国油画,又都是原作。喔!油画原来就是这个样,我那时就是这么想,油画册翻过不少,今日才见苏联油画的“庐山真面目”。每次到苏联馆去都像过节一样,那里热闹非常,游人如鲫,熙熙攘攘。走累了我们便席地而坐,一边看画,一边啃馒头喝行军壶的水,将简单的物质粮食和丰富的精神粮食一块吞下。
学校里规定每年有一个月的创作实习时间,到乡下去进行实地写生,这对我们每个同学来说是件兴高采烈的事。早早便做好准备,个个都想去画一大堆习作回来。久居都市,到乡下去换换环境,怎能不教我们这些学生感到兴奋呢。那叶家河的溪流、麻城的田野,至今难忘。从竹篱茅舍到一草一木,样样都觉得新鲜,从日出东山到夕阳西下,谁都不甘落后地一个劲地画呀画,用稚嫩的技巧去捕捉各自的生活感受,面对一条小路、一堵破墙、一个草堆,都会无端地激动半天,一画再画。
虽然不用参加高考,但我又一次面临选择——选择什么专业继续深造。版画挺有趣,中国画我也喜欢,中国绘画有悠久的历史,源远流长,有完整的理论体系,积累了极丰富的技法经验,并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作为依托,可以找到许多名家大师的原作精品以资借鉴。现今有许多中国人在从事中国画,简直是千军万马之众,只要做到全国一流,那便是世界水准了。
油画很有它迷人之处,但油画艺术在我国发展不过百来年时间,不说国外油画大师的作品极难见到,一般的外国油画原作亦不多见……冒昧说一句,平常能够见到的,大都是些土油画,要想在中国学习油画,只好从印刷粗劣的画册、图片去揣摩,怎么才能“土”出个世界水平来呢?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。
可是我又想,唯其困难可能才更有趣味,就当是一个蓝色的梦吧,或许到最后我只能成为一小块铺路的石,只要曾经为之奋斗过,也就心满意足了。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后,我在入学志愿表格上,一连填了3个油画,拿定主意,准备“不成功,则成仁”,就这样,我进了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。
我更喜欢四年级时的一张课堂作业,幅面不大的油画,叫做《稻香时节》,得稿于中山水乡,反映了我那时对乡村题材的浓厚兴趣,以及对表现人物的偏好,也是由生活到艺术的一次“现实主义”创作方法的具体实践。指导老师是尹国良,他在我众多小构图中肯定了这张画的苗头,让我发展成一幅完整的油画,整个创作过程我一直保持着高涨的兴致,对拇指大小的一张脸孔画得是津津有味,力求形象表情细致入微,那时毕竟精力充沛,像现在戴上200度的老花镜也不容易办到。这画完成后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充分肯定,曾在报上发表,由《广东画报》彩页刊出,成了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件藏品。
王肇民老师虽然未上过油画课,但教我们素描和水彩,他坚持言传身教,在课堂上学生画什么他画什么。绘画是视觉艺术,百闻不如一见,他这样做,使我得到很多直接的教益,它既不盲目崇拜也不排斥苏联教学方法,他自有他的一套不洋不土的方法。这方法的基础,我认为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东方艺术观。他强调对待模特要有主动性,对绘画的对象要做充分的理解。强调画家的移情作用,他说“人可以当物画,物可以当人画”。他不主张描绘得绝对准确,反对在同一个地方改来改去,“错就错了,将错就错,一错到底”——当然这是画画的道理,做人知错还是要改的。

1970年,也是在秋季,我从英德茶场的文艺干校借调回广州,在“省文艺办公室”指挥下干着“救火队”的工作,哪里任务紧急,就到哪里去干。差不多整6年没怎么画画。

正碰上鲁迅纪念馆要重新开放,我被派去帮助搞陈列,因为鲁迅先生晚年部分找不到合适的照片,要我创作一张鲁迅晚年的肖像画,于是我很当一回事地干起来。首先熟悉有关材料,跟着设计草图,制作色彩小稿,把在学校里学过的一套程序搬弄起来,别的什么都没考虑,抓起我已久违的画笔,一心只想过足油画瘾,进入创作的一种无功利状态。那幅题为《永不休战》的油画,就是这样在兴奋和轻松中完成的。以后,每当我创作其他作品,总想重新体验画《永不休战》时的那种创作心态,却很不容易。因为要排除各种杂念的干扰,就像在满是浮萍的水洼里掬一捧洁净的清水那样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