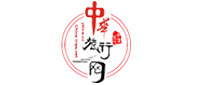张诺娅:中国女孩徒步穿越横着的珠穆朗玛峰
众所周知,张诺娅是唯一一个完成“三重冠”路线的中国女孩。在走上纵贯美国,全长4300公里的大陆分水岭步道之前,她曾充满感伤的说:“浪漫总是发生在远方,大陆分水岭将是一次物是人非的久别重逢。”而在这一次前所未有的140天的探险中,她经历的,不止是一次海拔升降相当于从海平面到珠峰上上下下15次的艰苦旅程,她也收获了自己的“Trail romance”,一个人的SOLO徒步孤旅,变成了两个人的牵手徒步,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,和喜欢的人7天乘以24小时的相处,一起用双脚把山野变成了脚下的艺术品。在加拿大边境首领山边哨卡的终点掏出中国国旗的时候,她最终承认:“人的故事,比风景更加刻骨铭心”。4300公里的山野之旅,从墨西哥边境到加拿大边境,这是她长距离徒步之旅的终点吗?或者只是另外的一个开端?对于这个向往着纯粹的自然主义,喜欢梭罗、爱默生的中国姑娘来说,探险的毒液,已经完全融入了她的血脉。还是被问了千百遍的问题,徒步的意义是什么?“不管你去或不去,大山都一直在那里,没有半推半就,不痛不痒,一拳一步,都是人生”。

此刻,我站在“三重冠”的终点“4300公里,140天,海拔升降相当于爬15次珠穆朗玛”说顺理成章,是因为自我2014年徒步太平洋山脊、2015年徒步阿帕拉契亚小径之后,该是给这“三重冠”收尾的时候了。说它突然,是我太清楚自己的斤两和局限,畏惧这条“横着的珠穆朗玛”。或许,在内心深处,也是害怕它结束,害怕三重冠结束。在美国,大陆分水岭可以粗略理解为落基山脉,西边的水域流向太平洋,东部的水域流向大西洋。CDT门槛高,目前完成的人数不超过400人,每年完成人数在10~30人之间。虽然CDT身为“国家步道”,但其自选线路眼花缭乱、补给偏僻稀疏、徒步人数稀少,基本没有辅助设施和步道文化。我在这场旅途中累计了600万有余的步数,海拔升降279645米,相当于从海平面到珠峰上上下下15次,穿坏了7双鞋,遇见过2头熊,在野外扎营100天,吃掉500多根能量棒。在四个半月的徒步中,我穿越了落基山、黄石和冰川3个国家公园,25片国家森林和4片国土局管辖属地,途经了美国的第一个荒野保护区——希拉河谷,也穿越了风景秀丽的圣胡安山脉、干燥的怀俄明大盆地、大岩壁和高山湖遍布的风河山脉、Bob Marshall马歇尔荒野保护区、“北方的珍珠”冰川国家公园等等。人文方面,它也经过了美国西部最有代表性的人文景观:失落的矿业小镇、摩门西征的遗迹、印第安人在岩壁上的家园……在大陆分水岭之路上,我每个月都需要攀爬雪山,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季,路线多在山脊之上,落基山脉夏季的风雨雷电成了旅途的常客。曾经24小时不见一人,也在找到徒步伙伴之后24小时面面相觑,只拥有彼此,路面包括了泥土、石子路、大岩石、草甸、雪地、冰面、树木倒伏遍地的森林、沼泽、和根本没有步道的荒漠、草地、山脊。曾经连续5天夜夜生火,最长的一天走了100公里,也有过被困在风雨中寸步难行的经历,在补给的时候做了几顿中国菜,泡了几十顿冷晚饭,在圣胡安喝了一礼拜没有净化的野生水,也被步道天使邀请到家里打地铺,蚊子最多的时候,哪怕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帐篷,也会带进去几十只嗜血狂魔,曾经在牛粪中醒来,一天磕过16片止痛药,也在攀岩之后以为队友挂了……人间,好像离我们很远。如今,我站在翻山越岭的尽头,回望CDT上的每一天。 出发 精疲力竭寻找藏水点炙热的高地沙漠在眼前铺展开来。我们9个人,在不成形的土路上颠簸了3个多小时,才站在国境纪念碑面前,遥望眼前这看不到边的北方。边境之内160公里半径的土地上没有自然水源,我们必须每天至少到达一个“藏水点”。中午没有蔽荫,找一块没有蚂蚁的沙地,把皮肤遮起来,露天席地躺倒三小时,等最炎热的时刻过去了,才能继续出发。翻越牛栏、铁丝网,在牛粪遍布的土地上绕行;有时候步道变得模糊,只得在广袤的荒漠上自己开路。精疲力竭来到第一个藏水点,取出三升水,全身已布满沙尘。

如果我没有哭出来,一定是因为路痴大爷在。担心了好几年的圣胡安山脉雪山穿越,真实情况竟然比想象中更艰难:每天早上5点在雪地中哆哆嗦嗦撑开已经冻成冰棒的跑鞋,穿上雪链,左手冰斧,右手登山杖。前方步道被积雪掩埋了,或是在陡峭的山脊侧腰,便和路痴大爷反复对照地图、GPS,选择一条可能更吃力、但相对安全的路线前进。绕着山腰的线路,被我们改成了直线下降到谷底、再从谷底爬上另一侧的山脊冰湖还未解冻,湖边的路线太危险,稍不留神可能就滑坠到冰冷的湖里,只得从原理湖面的树林中前行,一路还要翻过各种倒伏的树木。伍迪、迪伦几个快腿追上来时,我和路痴大爷刚刚横切了一个60度的雪坡。我说:对不起,我拖后腿了。路痴大爷好心安慰我,看我有点缺水,竟然把他的水给我,自己去悬崖上找水……南圣胡安的最后一天,我们离补给的高速路只有不到8公里路程,前方被危险的倒伏大树和陡峭的雪坡拦住去路。伍迪等留下了纸条,告诉我们他们选择直线下降到谷底的湖边,再从湖边连结到另一侧的公路上。下山的路虽然艰险,可我和路痴大爷万万没想到:湖边完全没有路,一侧是倒伏遍布的树林,一侧是冰冷的湖面。望着湖水另一边的公路,我恨不得游泳过去,或者呼叫救援队派送一条小船。可我知道,此刻惟一能做的,就是在荆棘和倒树之中寻找不掉进水里的路径,硬着头皮完成这一“不得不”去走的惟一路线。这时,一不小心在雪坡上滑倒,还好有几棵小树,拦在湖边。我下意识地用登山杖增大阻力,腿向下,头朝天,用背去撞树。最后的结局是:屁股上多了好多青青紫紫的伤疤,尾椎骨疼了几天,人倒是不偏不倚地卡在树桩上,没有滚进湖里……我没有哭出来。